閱讀雲門2月號|訪「雲門舞集」女團員—專業舞者的心聲
文字版請往下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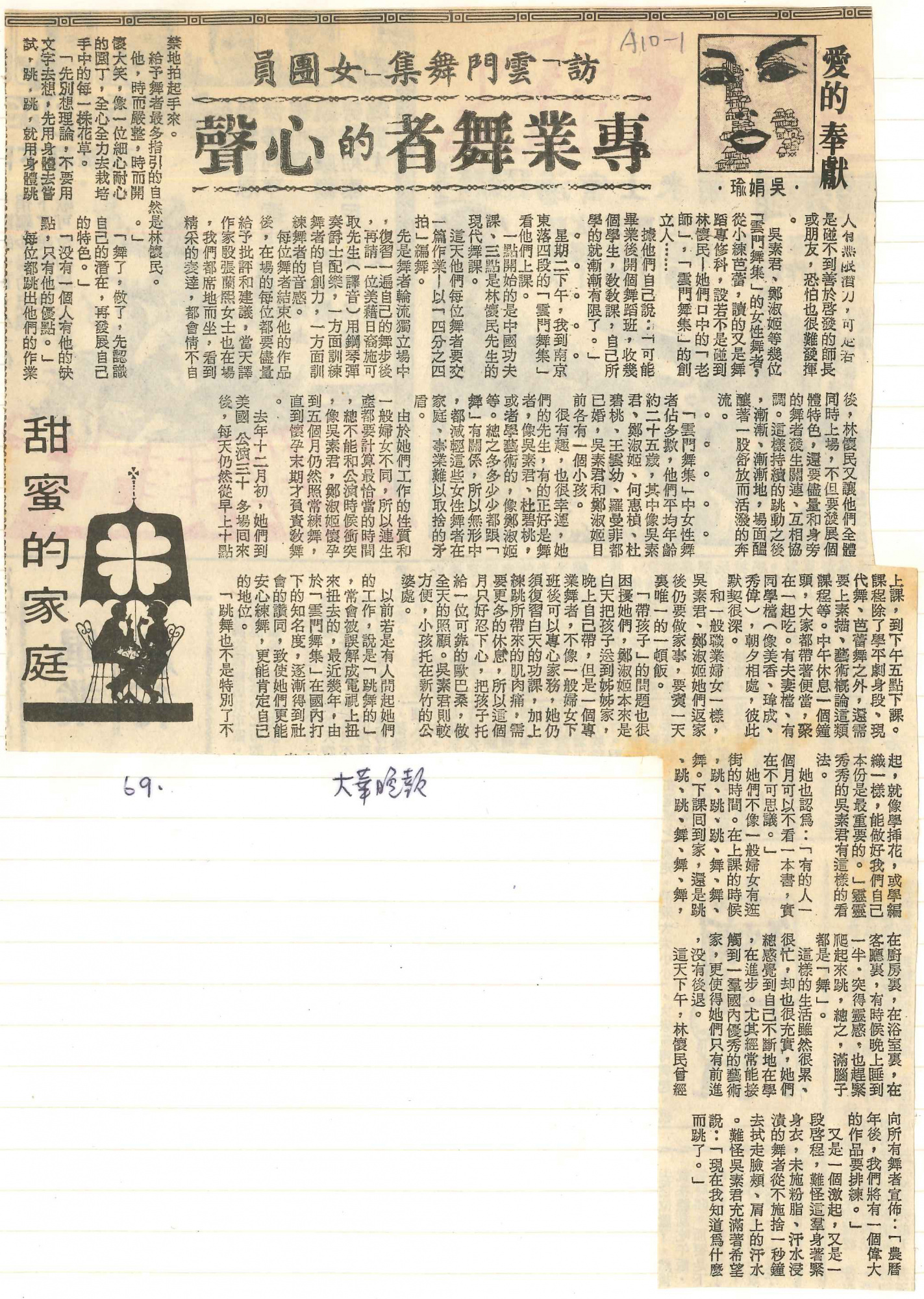
訪「雲門舞集」女團員-專業舞者的心聲
文/吳娟瑜 刊登於1980年《大華晚報》
人有無限潛力,可是若是碰不到善於啟發的師長或朋友,恐怕也很難發揮。
吳素君、鄭淑姬等幾位「雲門舞集」的女性舞者,從小練芭蕾,讀得又是舞蹈專修科,設若不是碰到林懷民-她們口中的「老師」,「雲門舞集」的創立人⋯⋯
據他們自己說:「可能畢業後開個舞蹈班,收幾個學生,教教課,自己所學的就漸漸有限了。」
。。。。。
星期二下午,我到南京東落(原文有誤,應是「路」)四段的「雲門舞集」看他們上課。
一點開始的是中國功夫課、三點是林懷民先生的現代舞課。
這天他們每位舞者要交一篇作業-以「四分之四拍」編舞。
先是舞者輪流獨立場中,複習一遍自己的舞步後,再請一位美籍日裔施可取先生(譯音)用鋼琴彈奏爵士配樂,一方面訓練舞者的自創力,一方面訓練舞者的音感。
每位舞者結束他的作品後,在場的每位都要盡量給予批評和建議,當天譯作家殷張蘭熙女士也在場,我們都席地而坐,看到精采的表達,都會情不自禁地拍起手來。
給予舞者最多指引的自然是林懷民。
他,時而嚴整,時而開懷大笑,像一位細心耐心的園丁,全心全力去栽培手中的每一株花草。
「先別想理論,不要用文字去想,先用身體去嘗試,去跳,跳,就用身體跳。」
「舞了,做了,先認識自己的潛在,再發展自己的特色。」
「沒有一個人有他的缺點,只有他的優點。」
每位都跳出他們的作業後,林懷民又讓他們全體同時上場,不但要發展個體特色,還要盡量和身旁的舞者發生關連、互相協調。這樣持續的跳動之後,漸漸、漸漸地,場面醞釀著一股舒放而活潑的奔流。
。。。。。
「雲門舞集」中女性舞者佔多數,他們平均年齡約二十五歲,其中像是吳素君、鄭淑姬、何惠楨、杜碧桃、王雲幼、羅曼菲都已婚,吳素君和鄭淑姬目前各有一個小孩。
很有趣,也很幸運,她們的先生,有的正好是舞者,像吳素君、杜碧桃,或者學藝術的,像鄭淑姬等。總之多多少少都跟「舞」有關係,所以無形中,都減輕這些女性舞者在家庭、事業難以取捨的矛盾。
由於她們工作的性質和一般婦女不同,所以連生產都要計算最恰當的時間,總不能公演時候衝突,像吳素君,鄭淑姬懷孕到五個月仍然照常練舞,直到懷孕末期才負責教舞。
去年十二月初,她們到美國公演三十多場回來後,每天仍然從早上十點上課,到下午五點下課。課程除了學平劇身段、現代舞、芭蕾舞之外,還需要上素描、藝術概論這類課程等。中午休息一個鐘頭,大家都帶著便當,聚在一起吃。有夫妻檔、有同學檔(像美香、瑋成、秀偉),朝夕相處,彼此默契很深。
和一般職業婦女一樣,吳素君、鄭淑姬她們返家後仍要做家事,要煮一天裡唯一的一頓飯。
「帶孩子」的問題也很困擾她們,鄭淑姬本來是白天把孩子送到姐姐家,晚上自己帶,但是一個專業舞者,不像一般婦女下班後可以專心家務,她仍須複習白天的功課,加上練跳所帶來的肌肉痛,需要更多的休息,所以這個月只好忍下心,把孩子託給一位可靠的歐巴桑,做全天的照顧。吳素君則較方便,小孩托在新竹的公婆處。
以前若是有人問起她們的工作,說是「跳舞的」,常會被誤解成電視上扭來扭去的,最近幾年,由於「雲門舞集」在國內打下的知名度,逐漸得到社會的讚同,致使她們更能安心練舞,更能肯定自己的地位。
「跳舞也不是特別了不起,就像學插花,或學編織一樣,能做好我們自己本份是最重要的。」靈靈秀秀的吳素君有這樣的看法。
她也認為:「有的人一個月可以不看一本書,實在不可思議。」
她們不像一般婦女有逛街的時間。在上課的時候,跳、跳、跳、舞、舞、舞。下課回到家,還是跳、跳、跳、舞、舞、舞。在廚房裡,在浴室裡,在客廳裡,有時候晚上睡到一半,突得靈感,也趕緊爬起來跳,總之,滿腦子都是「舞」。
這樣的生活雖然很累、很忙,卻也很充實,她們總感覺到自己不斷地在學,在進步。尤其經常能接觸到一群國內優秀的藝術家,更使得她們只有前進,沒有後退。
這天下午,林懷民曾經向所有舞者宣佈:「農曆年後,我們將有一個偉大的作品要排練。」
又是一個激起,又是一段啟程,難怪這群身著緊身衣,未施粉脂、汗水浸漬的舞者從不施捨一秒鐘去拭走臉頰、肩上的汗水。難怪吳素君充滿著希望說:「現在我知道為什麼而跳了。」